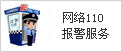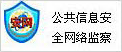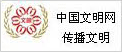在我的意识中,从没有性别差异的问题。直至一九九五年参与世界妇女大会时,所谓的「女性意识」才真正…

促进女性地位 全赖民改教育
在过去,彝族社会只有所谓的女性“德古”(调解纠纷的人)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其它诸如打战、议事、决策等,则是男性的世界。
然而随着民主改革,以及男女平等观念的提倡,妇女遂得以进入公共领域,社会地位亦因此方得以伸张。
此外,彝族女性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亦是其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现今社会乃以考试取决胜负,女性因而更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并且激励妇女,据此大量进入国家机关从事公职或教师、乃至深入企业等各不同领域中,充分展现能力。
另外就是机会。我与妹妹算是机遇不错的人,例如大学推荐甄选时,虽说我们均须有个人的准备,但若未事先获得学校推荐,我们根本无法在所有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而我个人,有幸在每个人生阶段都还顺利。因此,从学士毕业到宣传部工作,然后再一路从硕士、博士到出国留学,之后却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国家机关里发展。
坦白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机遇与成就。这些或许是女性主义潮流的影响,但我认为政府的大力提倡,才是关键。
意即,政府的政策给予我们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个人亦懂得抓住此一机会,再加上自我的努力,才可能会有日后美好的果实。
彝族女性社会地位优于汉族
当然,彝族妇女地位仍然普遍存有城乡差距的问题。其中,最突显的即在于婚姻决定权方面:以凉山为例,农村社会的妇女,仍旧是停留在父母包办的情况。
彝族的传统属于父系社会,两性地位与汉族结构差别不大,都是男尊女卑的观念。每个家庭都是由男性主导,特别是交易等经济大事,即由男性决定。
妇女在许多方面,都不具名分与地位。例如进入夫家后,她不能拥有个人财产,却必须承担家务、奉养翁姑、教养子女、从事农活…
相较于传统汉族社会,妇女总被认定是既已泼出去的水、终其一生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彝族妇女在某一程度上,其所受到的保护,还是比较优于汉族女性。
婚姻在彝族社会的精神,乃是家庭的传承与延伸。他们咸认:婚姻不单只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
因此,若是彝族妇女出嫁之后受到夫家欺负,她的娘家兄弟必定出面讨公道,例如将他们的家放把火烧了、甚或把鸡鸭等家畜带走…等等诸如的做法。由此可见,汉族妇女与彝族相较,确实有着天壤的待遇。毕竟,彝族母舅在某一程度上,确有其绝对的地位与影响力。
再者,地位的高低亦与其经济能力息息相关。城市中的妇女经济可以独立,社会地位自然高一些;而在农村,则仍然承袭传统的观念,加上经济水平较低、毫无自主能力、生活圈狭小,妇女只能被家庭制约,地位自然差一些。不过最近已有些彝族妇女,放下过去的传统观念,将田间工作所得拿去贩卖,手头既然有些私蓄,当然也就拥有一些自主权力。
至于彝族女性在汉族社会中是否得到尊重?我想,一个工作勤奋的人,必然会受到尊重。
身处汉族社会中,当然会被视为“少数民族”,也多少会有些许歧视的眼光,但是当对方发现你各方面的能力与他相当,甚至比他还强,自然会尊重你。
母亲坚毅的引领 造就彝族首位女博士
不论是女性,抑或是男性,每一个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母亲通常扮演着极为决定性的关键,我的母亲亦如是。
尽管母亲只有初中的教育程度,但她很了解教育的重要,她并且深知:纵使少数民族有政府的帮助、社会的捐助,若是没有充分且平等的教育机会,恐怕还是难以改变根本的命运。
回顾四岁时,我被父母送到姑母住的小乡村。但是当时幼小的我,心底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西昌。
因为在彝族的宗教驱鬼仪式中,总认为只要把鬼赶到热闹的地方,他就不会想要再回来。而西昌正是个吃的、玩的都很多的热闹城市;因此,族人便都是把鬼赶到西昌去的!
直到念小学后,母亲发现我的错别字特别多,心想若是让我继续待在那儿,恐怕会耽误了我的前程,于是便随即将我从姑母住的小乡村接回家,我因此终于有机会来到凉山的首府“昭觉”读书。
刚进昭觉小学,我是成绩最差的学生。当时又碰上母亲要回内蒙娘家,老师提醒我:“成绩那么差,别回去了,你现在还赶不上别人呢!”我说:“我回来再努力,肯定会赶上同学的!”结果考初中的时候,我是全年级的第四名。
读高一的时候,我便已通过大学推荐甄选,但高中毕业时,并无心继续升学。况且,那又是彝族孩子首批被送进大学里的,因此当时并不觉得读大学有什么必要。反倒是一心只想着:只要学跳舞唱歌,便可以早一点就业。
于是当宣传来招生之际,我特别选了唱歌跳舞的科目,然而母亲不允,不让我自作主张。母亲当时心特狠的,我天天在她的床边哭求,即连父亲都动了心,还出面帮我向母亲说情;但她仍是坚持要我念大学。
胞妹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初中毕业的时候选择当护士,并不想读高中,因为她认为自己笨。母亲却说:“你笨鸟先飞,还是去考高中吧!”
如今再回首当年,能够到西昌就已经是个极大的梦想。没想到现在,我不单只是去过西昌,并且还去了成都、北京…甚至足迹已然遍访过海外,二、三十个国家以上。
身为少数民族的我,因着母亲坚毅的引领,让我获得充分的教育,即是改变我个人一生命运,重要的转折关键。
专研彝族文化 再创历史新猷
我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高中毕业后,随即进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就读。民族大学是个多元的学校,拥有来自各地不同民族的学生,也因此启迪默化我后来的学术方向。
犹记得大学毕业后,我便又回到凉山,旋即进入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两年。身为第一批大学生,又是少数民族女性;按理说,在仕途上应该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而我的父亲当时刻正担任西昌市的市委书记,更可顺理地成为我的靠山。
然而父亲当时深感:彝族人士在民改之后,担任地方干部的较多,但从事自身民族研究工作或高等教育者,却寥寥无几。
回溯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并不重视少数民族。直到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少数民族文化才又获得尊重,党的民族政策也才落实。
因此,父亲建议我继续攻读研究所,专事研究彝族文化。他说:“没有几个搞彝族研究,能像?这样搞的,?还是好好的做研究吧!”
我遂听从父亲的建议,积极考进彝文文献研究所,成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彝文文献领域的研究生;同时也是彝族,第一位专研女博士。
遗憾的是,唯今专研此一领域的博士,仅有我一人;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业已故去,因此也就无法再招收新学生了!
我研究的是彝文文献,胞妹则是研究彝文文学。我们在村里搞田野调查时,经常是湿着身子回到家,母亲见了不忍,流着泪说:“别人家的女儿都是学经济,然后出国深造,你们却是天天往村子里跑。实在不理解你们父亲,为何把女儿拴着做这些苦差事儿。”
后来在一次彝学研讨会中,母亲不断地听到与会学者啧啧称赞:他们好父母俩,很有远见地鼓励女儿从事彝族文化研究,并且做出好成绩…至此她才终于理解,女儿走的方向是对的。
事实上,我们研究彝族文化,同样大步走出国门,不仅到哈佛继续深造,还到各国办展览、开研讨会…而国外学者来到中国研究彝学,我们更是扮演中间的桥梁。
我认为一个人,唯有深入了解其自身文化、族群历史…他才会有能力为其现今所处定位,也才能充分掌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女性慈慧特质 社会发展元素
平心而论,长久以来我虽多与男性同学或共事,乃至相互竞比。但在我的意识中,却从没有性别差异的问题。直至一九九五年参与世界妇女大会时,所谓的「女性意识」才真正从我的脑中蹦脱出来。
此外在职场上,正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更应该努力、更要做得不比别人差,故此从不觉得受到性别歧视。这种感受,也或许是基于个人的工作环境、机遇与自身条件吧!
况且,我身兼母亲的角色,自然在工作中流露慈心与认真,对别人更能体贴、关爱,更执着奉献与回馈的精神。
例如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只要是我负责辅导的学生,我便会执意:一定非得让他拥有通过考试的实力。因此经常为了陪读,乃至逢年过节我都是从家里搬着锅子,到教室里煮食给学生们裹腹。
因为做母亲的人,往往想表现给孩子好榜样、好形象。即便是自己稍有不好的念头,亦都会及时的压抑下来,尤其是指导学生的时候,这种心理特别强烈。
常有人会问:如果有一天必须在婚姻与工作间,只能选择其一,我将会如何做抉择?
基本上,我不认为自己会面临这样难堪的问题。但是,假设果真让我遇上了,我想婚姻还是比较重要吧!
因为在家庭里,我仍然可以回头做学术研究。设若把婚姻、家庭丢弃了,那么人生路上我可以选择的,将会很窄小…
不讳言,大多数人的矛盾总是把家庭、婚姻,甚至把最关爱的人,放在最后头。
殊不知,实际上他们才是整体国家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元素。
巴莫阿依简介:
现任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司副司长。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也是彝族第一位女性博士。
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1991年荣获文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00-2001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曾深入中国西南彝族、纳西族、日本东北部和美国西雅图,以及欧洲各少数民族等地区,进行宗教、田野调查与研究。
并于1997年、1998年两度受聘于世界银行,担任安宁河流域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大型项目的社会评估工作和拟订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主要从事宗教学和彝族宗教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兼具学术、著作等身,个人出版专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译着《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合着《彝族文化史》、《彝族风俗志》等。
并在《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宗教学研究》、《民族艺求》、《比较民俗学》(日)、《美中社会与文化》(美)等刊物,定期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五十余篇。
贵州文化网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闻权威媒体,贵州文化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进行学术交流之目的,并不用于商业用途且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如果侵犯贵处版权,请与我们联络,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本站出处写“贵州文化网”的所有内容(文字、图片、视频等)均受版权保护,转载请标明出处和作者。
> 相关文章
-
无相关信息


 贵州大学教授金智超:做接地气的科研..
贵州大学教授金智超:做接地气的科研.. (东西问)范红:中国村级赛事何以引来世..
(东西问)范红:中国村级赛事何以引来世.. 贵州黎平吴开勇:二十七年用心育苗 ..
贵州黎平吴开勇:二十七年用心育苗 .. 守好文物尽己责—吴隆灿..
守好文物尽己责—吴隆灿.. 论道专访︱范同寿: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
论道专访︱范同寿: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 把脉问诊护航安全的铁路女首席工程..
把脉问诊护航安全的铁路女首席工程..